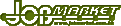手術後,病人瞳孔稍稍變小,對光也有反射,可是卻沒有醒來,我的心沉得像灌了鉛,儘管中午到現在都沒吃,卻沒有絲毫的飢餓感,而想吐的感覺卻越發的明顯,我擔心病人再也醒不過來。家屬們圍在病人的床邊,有時會向我望來,迫切的眼神好比探照燈,我成了一個光圈中的小丑。手術前保證「我會盡力」的聲音,此時在我腦海中歇欺底里的吼叫。
到了深夜,病人瞳孔再次放大,再一次的電腦斷層掃描顯示剛清除完血塊的地方又再出血,而且比手術前的更大,病人昏迷指數掉到三分。夜半加護病房外的迴廊格外的安靜,我可以感覺到自己不安的心跳,一群家屬圍着我,我是那一個該打靶的紅心。我說:「病人也許回不來了。」是上帝借了我的口宣判病人死刑還是我自己在扮演上帝?病人的女兒抱着父親放聲大哭,哭聲在幽黑的走廊裏不斷的回蕩,聲聲斷腸。而我,一個醫生,不過是一個棒棒糖掉在地上的小孩,無能為力。
三天後病人去世。享年四十三歲。我非常的沮喪失落,經常想到一個沒有太太的丈夫和少了媽媽的女兒,連做夢都夢到替病人緊急開刀。看到孩子時虧欠,面對病人時自責。聽了女兒在車上說的那番話,我很想和她說:「爸爸也希望自己不是醫生。」直到有一個晚上,我替一個從高處墜落的一個八歲小朋友動完手術回家,已經是凌晨三點,身心疲憊不堪,一整天沒有看到妻子和小孩,再想到手術完那個小朋友不知道會不會醒,我全身的力量彷彿被抽盡。太太在玄關給我留了一盞燈,我打開鐵門,昏暗的燈光下,地板上留了一張字條,是兒子的字跡,寫着:「爸爸,我希望你已經回到家。就像你知道的,我已經睡着了。我希望你的手術順利。」握着他的留言,眼淚突然奪眶而出,我跪在地上,捲縮在門邊啜泣。
我是醫生,我想背着每一個病人過河,日子久了我明白,不是每一個病人都過得了河。
電郵:eacorp@breakthrough.org.hk